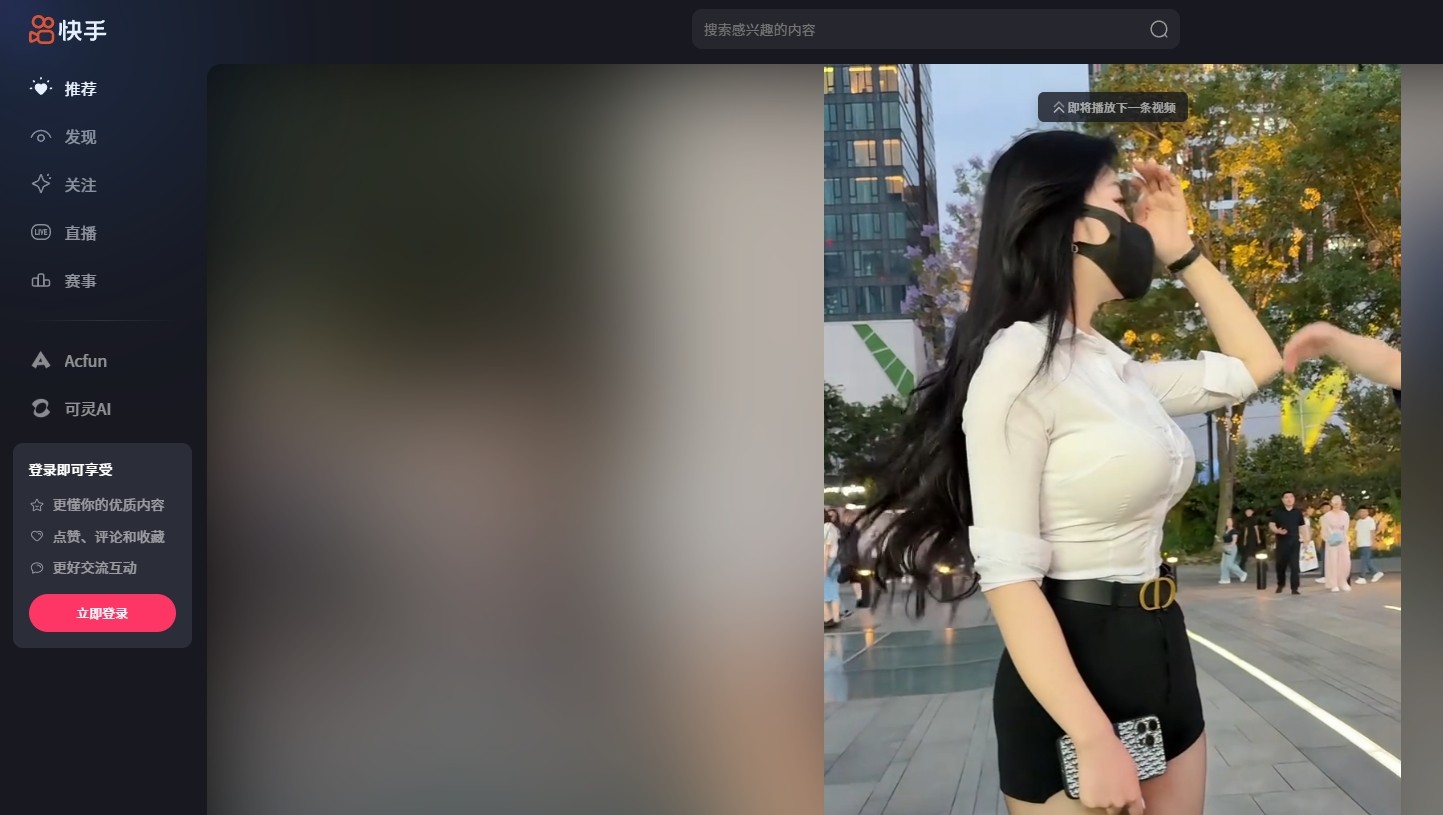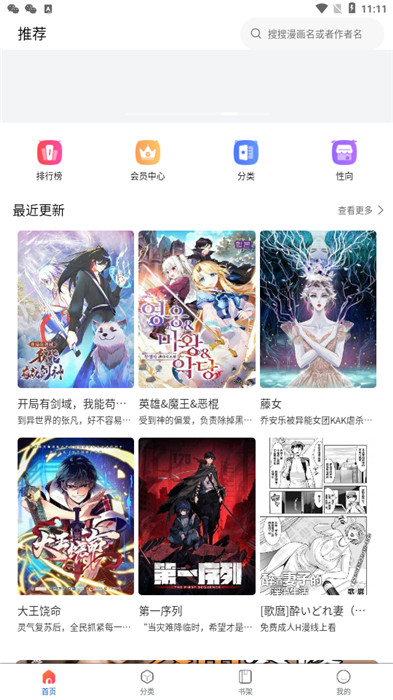高三优秀作文:悲悯与幸福
“我真的很讨厌在过节的时候见着这些人…”我拽着女友的手肘子飞快地走过蹲在一破篮子边,守着几只不很好看的苹果发着抖的老奶奶,一边皱着眉头一边说着,“影响心情。”
心像刚上幼稚园的孩子,轻盈盈的肩突然落上有分量的“担子”,感觉纠结复杂——苦于负担的沉重,又得幸于能担当的自我成长感。
人走在世上,经历世间万象,不觉就又多背了“担子”,多了悲悯,却也多了博大的幸福。
学校里住着一户承包教室卫生的保洁人员,每周六下午挨个打扫教室。有一回我留校自习,刚好遇上了那户的中年男人带着三四岁的小女儿来打扫教室。男人干活,小女孩则东摸摸西看看,不时捡起地上吸引她的小玩意把玩一番。我一直用视线跟踪着女孩,看见她眼睛一亮地从椅子下抓起一个看起来已经瘪瘪的饼干包装,小心翼翼地将内盒全推出来,抓起已半露在外的有些脏兮兮的小块饼干就要往嘴里送,这时男人一个箭步迈过来夺走饼干,我想着,这还差不多,地上的垃圾多不干净。哪知,男人只是细心地吹去饼干上的灰尘,一边用指腹轻拂着一边在空气中狂甩几下,再温柔地把饼干送回到女孩的嘴里,自然地微笑着。
我坐在教室的最后面,看着穿着脏兮兮工作服的男人和脸颊灰扑扑的女孩吃饼干,感到酸涩难过。我想起刚被我丢入垃圾桶没怎么动的一大袋蛋糕,狭隘地感到庆幸:庆幸我不是在社会底层为温饱挣扎的人。但更多地,同情和怜悯趁机爬上心头,几近吞噬我——以男人和女孩为缩影,有多少人,在我所无法想象的社会黑暗里,为起码的生存痛苦地摸索。然而,再回想起二人的笑容,心又是归于轻快的幸福感:生活,不论质量好坏,富足拮据,总有同等珍贵的真情。
我想起曾在杂志上看到的父母双亡的艾滋病儿童,他上被隔离的一个人的学校,在僻远的山区里过着被人情排挤的生活。每天升起的太阳对他来说都可能只是上天恩赐的巧合,生命,从来没有给他承诺。报道的最后是一张黑白照,男孩攥着他唯一的玩具——一只悠悠球,笑着,像所有生命力旺盛蓬勃的普通孩子一样充满希望。
我很没有用地落了泪。我又在狭隘地感到庆幸,庆幸我身体强健,我活着,还有一个未来在等我去追,还有一大段漫漫人生路在等我认真去走。另一个角落,我的心在控诉,控诉生命的不公平——他给人没有选择的伤残病痛,给人打折的人生期限、降价的微薄幸福。可最后,颤抖着的怜悯和悲叹平静下来,又是复归于感激,感激生命不论时间长短,安乐苦痛,总有希望和阳光。生命总也还是公平,拥有哪怕只有一小撮人生,也还是觉得幸福。
“凡深刻的世界观,所达至的必然不只有快乐,必然还有对人世博大的悲悯。”周国平先生这样说。幸福和悲悯,悲悯和幸福,这是一个情感复杂的循环:在对比中发现幸福,发现被忽略甚至视为理所应当的生命精华,然后在幸福中控诉黑暗和不公,悲悯于万物生灵,于是发现自己的心灵多了与苦难共鸣的沧桑,多了成熟和思想担当的生命的重量,又带着悲悯和幸福再循环。